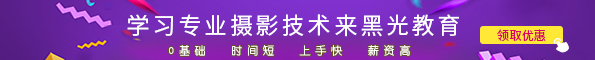小编:中国有没有摄影流派?
蔡萌:要说的话,应该有,比如说三十年代民国时候的画意沙龙摄影,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人画基础上的,比如郎静山他们当时在做的那批东西,那应该还算是中国的一个,典型的具有东方独特审美美学标准的摄影,它具备一个流派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说美学趣味,包括群体的规模,包括参加的展览,甚至获得国际的影响、认可,我觉得甚至它那种影响几乎一直贯穿到现在还在影响。
小编: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行为摄影,像《为无名山增高一米》、张桓的《十二平方》这种照片,从严格意义来说它应该算是观念摄影还是艺术文献?
蔡萌:从两个角度来讲都有可能有这种意义在里面,从文献的角度当然是文献,它是有记录性的,记录了一个行为艺术的过程。要是说从艺术角度来讲,首先它有两种可能性作为艺术,一种是说它有一个很好的摄影家在拍,然后摄影感觉很好,它有一种艺术性。另外就是它的内容本身具有一种艺术性,就是所有人在照片里表演,其实某种程度上摄影就是被拍摄者在照片里表演,拍摄照片的人能够干预和驾驭这张照片的因素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表演本身是一个非常当代的一种艺术的方式,所以它同样具备了这样艺术的特征。
小编:您在《观念摄影在中国》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中国摄影对西方的一种依赖,是处于迎合西方的一种状态,目前来说对于中国摄影艺术是西方关注大于本土关注吗?
蔡萌:也不能这么谈吧,因为我觉得本土现在对当代摄影这块也挺关注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比如从市场的角度来讲,西方关注确实大于本土,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中国摄影80%多的藏家和买家都在海外,甚至到90%都是外国人。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这种影像方式,关注这种图像方式,甚至去模仿这种成功的经验,去抄袭和模仿前辈们的这些摄影家,像王庆松,像苍鑫、洪磊、洪浩、黄岩,当他们的图像变成经典之后,就变成了后辈的年轻人学习、模仿、参照的一个对象,被更多的年轻人所关注。在现在高校的摄影教育,甚至是在摄影节上,尤其像平遥摄影节,你会发现貌似这种观念,这种当代艺术的摄影现在是非常的普及,叫现代版的观念摄影吧。今天我们都强调观念,要做摄影的话,上来就说观念最重要,我们都认为观念重要,而这种观念的东西呢,每个人似乎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