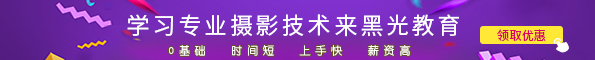小编:这段时间摄影艺术史的沉淀,对拐点之后的数码时代的审美观、艺术语言会有影响吗?
蔡萌:我觉得是看需求吧,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悖论,我们在谈数码完全可以不参照摄影,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当然,如果说我们现在都在遵循被商人绑架了的摄影摄影概念,去做数码摄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既然要认同数码摄影的话,那还是应该把传统的银盐再过一遍,知道它的语言边界之后再去做,可能会更有的放矢,或者是更能够找到一种语言的逻辑,或者是一种上下文的关系。当然我也在谈,数码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概念,完全是全新的东西,比如现在有些多媒体的展览,打的那种在墙上一个立面的一个巨大扫描仪,每个人上去扫一下,马上瞬间出现一个影像,或一会儿谁上再扫一下,又出现另一个人,我觉得那才叫数码。我觉得它不需要什么语言,不需要什么法度,不需要任何的一个标准,完全是可以跟大众拉近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这就是当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一个最典型的特点,被拉平了,艺术不再变得那么居高临下、高高在上,被膜拜,有一种压迫感。现在是一个艺术变得非常的大众化的时代,变得非常有亲和力,任何人都变得很接近,很容易让人理解,很好懂。
小编:中国的当代摄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四月影会”算不算一个开端?
蔡萌:最早是从“四五运动”开始的。因为“四月影会”还是一个跟“四五运动”有关系的群体,所以我更愿意把开端说成是“四五运动”,而且“四五运动”很明显把摄影完全从国家的权利话语迅速变成一个年轻人的个人话语。
小编:“四五运动”之前摄影应该算是官方统治的一个工具了。
蔡萌:对,但是“四五运动”、“四月影会”之后其中很多人又进到体制了,又回到一个权利话语的体系了,这当然是另当别论。但是就总体来讲,我所认同的当代摄影应该包括这两个类型,一个纪实的,一个是当代艺术的观念摄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五运动”肯定要放进去了,这种记录的,或者文献的摄影,典型应该放到当代摄影的总体的生态范畴里。但是作为当代艺术的这种所谓的观念摄影,我倒是觉得“四月影会”里头会看到一点点小苗头,它跟“八五新潮”里面出来的,作为当代艺术后来出现的这种摄影,他们之间其实还是有一些隔阂,这两个,它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但是他们两个群体里头到底有多少交叉还不好说,会有,比如说85年的时候,“四月影会”里面的林飞就曾经和中央美院的洪浩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