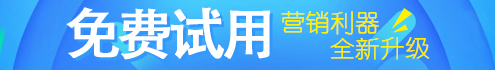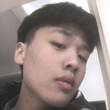2010年的中国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摄影事件:第八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先后有三位得主因被发现作品存在“违规”而被取消奖项,国展艺术类金质收藏作品《明天的现实》因“挪用”他人素材而被撤销资格;8月,颇具道德教化意义的《挟尸要价》在获得“金镜头”奖项之后,也在真实性问题上饱受质疑,并引起舆论的密集关注。连同此前发生的“藏羚羊”“广场鸽”和“周老虎”等假照片事件的层层累积,摄影的真实性,屡受质疑。
在影像真实屡遭冒犯之时,摄影以真实建立起来的权威和尊严也随之受到一次次损伤,而每一起假照事件的发生,因公众的热切关注也迅速转变成社会事件,进而使原本属于传播领域、艺术领域抑或专业领域的摄影问题,演变为关涉公众利益的社会性问题。
如同新政往往都萌生于乱世。在摄影真实的公信力屡遭破坏之际,2010年的中国摄影界也通过种种努力做着补救和修复的工作。这其中既有深入的理论探讨和严肃的规范研究,也有以强调关注现实、真实记录时代变革的各种摄影实践、展览以及评比活动的次第展开,热爱摄影和依据摄影获得价值与尊严的人们,希望借此渐渐恢复摄影的元气和固有的力量。
当然,造假事件已然成为一个由头,但属于摄影自身真实与真实性问题的深刻反省,却需要我们娓娓道来。
反省一:媒介与艺术
单一与偶然的事件,只能说明个案的特殊性,由此起彼伏的个案形成的普遍现象,则一定喻示着:历史的传统习俗和现实的世俗需求之间,潜伏着一条彼此切合的线索。
在违背摄影真实的“造假”事件中,对于为何造假的疑问,人们普遍认同当事人名利欲失控这一结果。但细细分析,普遍的个人问题也是群体观念和历史意识长期浸染的结果。就事论事和简单的一个“假”字可以迅速定论事件的性质以在表面上平息舆论,却不利于对事件本质的深究以避免效尤者的产生。在造假事件中,除了明显失实和事实造假等原因,尚有版权分割模糊导致的纠葛、评选标准含糊导致的误判,而以追求所谓的艺术完美来对图像展开的增减修补,乃是养成习惯并长期被忽视的一种现象。
删减、增补、添加……为何如此造假?为何坚持非如此就不足以认为照片是好的?为何坚信他人尤其是对照片意义具有“终极评价权”的人也会抱持同样的观点?其次,经过改动的照片,为何就称之为“假”?真的标准又是什么?假,又是假何物(对象)之假?难道是艺术?的确,在被尊为“艺术”的摄影中,类似的“改动”习以为常并引以为傲,然而,艺术手法在以求真为目的的摄影中,可否使用?如果可以,又当如何使用?
在摄影自身的真实性问题久存未决、难有定论的前提下,摄影之真与属于艺术的摄影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也可以如此发问:摄影在追求真实和向往艺术之间,是否存在一条自然的通道?是否有二者兼得、两全其美的可能?如果这个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追求艺术是否也就意味着摄影的真实性必将遭受损伤?或者说,追求真实就不能同时假借、兼具艺术之名!?以近些年中国摄影的假照事件而言,是否存在对艺术因素的过多考虑而导致了作品失实的情况?
所有的问题,都不能以“是”或者“否”来作轻率的了结,而追溯历史,却可以让我们的认识渐渐明晰——摄影的真实,在它作为不同的身份、力图承担不同的功用时,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和标准。
摄影、艺术和真实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纠葛,必须追溯到摄影与绘画之间缠绵已久的恩怨。画意摄影几乎就是今天所有的摄影流派得以生成的起点(其实它源自更早的“高艺术摄影”),拼贴、叠合以营造绘画效果的痕迹与遗韵,绵延流长,至今不绝。摄影的历史,由此分化转型,多种流派于是各成体系,其中成为主干的,恰恰就是中国摄影语境中所谓的艺术摄影、新闻(纪实类)摄影。
画意摄影在19世纪80年代渐趋成熟,包括自然主义摄影、印象派等风格和组织,均属于广义的画意摄影,具有极高的地位和价值,而同时期以写实为主的纪录摄影,比如拍摄战争的罗杰·芬顿们,则被视为不入流,成为零星散居的孤独者。直到斯蒂格利茨的出现,和他与影画双修的天才爱德华·斯泰肯在19世纪90年代合作掀起摄影分裂主义的大旗,尊重摄影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追求纯粹的摄影以独立于绘画之外的观点才渐被认可,并逐步建立起了摄影史上极具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20世纪20年代,保罗·斯特兰德等人又创立了直接摄影的风格,讲究摄影的纯正,“纯正,也就是视觉强度……它要求不带有任何制作和控制的痕迹。”这期间,同属直接摄影先驱者的爱德华·韦斯顿结合了一批愈加厌倦以柔焦造成画意效果的摄影师,成立了F64小组,主张以最小的光圈获得质感鲜明的表现力,安塞尔·亚当斯、伊莫金·坎宁安等一批未来大师的加入以及他们的非凡实践,使摄影忠于视觉观看的观念日渐普及,也导致了摄影历史和摄影理念上的重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