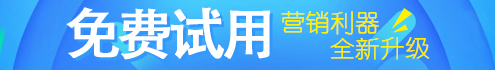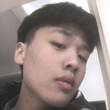八月国际影会,卢广也在大理。晚上七八个摄影家同桌吃饭,突然说是收到一条短信,焦点访谈正在播他的采访。放下碗筷,丢下众人,急急的跑下楼去。在大理古城的一个饭馆里,刚刚下过雨的瓷砖地板踩的黑乎乎,湿淋淋的。24寸的彩色电视里,有着石油事故中悲痛欲绝的人。站在下面看了七八分钟,一直到节目结束,出现剧务的名字,但是还未出现卢广。“我的采访在上半段,已经结束了。”卢广这样的跟记者解释。随之,怏怏的走上楼去。
卢广并不是一个感性的人,他处理不了细微的关系,不管是人与人,还是人与事。从这件小小的事情中,就可见一斑。
在他所有的拍摄过程中,尽管其过程是审慎并且细致的,用他的话来说,按快门只是一刹那,更多是在做调查。但是其思考的方式总是缺少一种慎密高深的神经。这几年自由摄影人的生涯,给了他很多出生入死惊心动魄的经历,采撷其中的任何一段都足以让一个记者写上半天。然而在他所有的叙述中,更多的是将那些苦难和真相呈现给我们,而绝少出现更深刻的关于经济层面,制度层面的分析和探究以及人类更具普遍意义的痛苦与和解。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卢广的这种特质帮助了他。他的粗疏,甚至某种粗糙给予了他最大的保护,让他看到那么多人间地狱后,免于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纠结和困扰。他的痛苦是真实的,正如他在看到瑞丽那些吸毒者满身的脓包后所表现出的痛心疾首。然而这种痛苦是可以排遣的。比如说,给那些人买消毒水,帮助他们医治,减缓他们暂时的疼痛。或者有关部门开始给予这些人补助。
人到达更普遍的宗教意义上的痛苦与和解或许有很多种方法,思辨是一种,实践是另一种。
荷赛的奖项,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这大大小小的奖项给卢广带来了众多的争议。很多人都开始将焦点集中在“卢广拍摄中国的污染和黑暗,是不是为了取悦国外的评委,为了拿奖。”而在国内很多的媒体上,大家也把这个作为一个舆论的焦点。我们这个世界有金钱的既得利益者,有政治的既得利益者,卢广只是拍摄了真相,如果这个事情让他有了名气和地位,那么作为拍摄真相的既得利益者,又有什么问题?
卢广的动机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人的心如深埋在大地下的树根,枝枝蔓蔓,复杂而庞驳。拷问一个摄影师拍摄的目的对于我们的意义其实并不是那么大,将道德的利剑悬于事件之上显得有点本末倒置。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公共背景下,关注那些镜头下的真相和解决暴露出来的问题才是一个共同的困境。当然,放在摄影这个专业领域内,我们可以去探讨画面的来源和出发点。卢广说了,他不追求真实的瞬间,但是追求真实的事件。
记者眼中的卢广有一种草根式的理想主义者情结。他没有更系统的知识背景和文化修养,但是却有一种强大的本能般的直觉,而他凭着一种冒险家般的执着,用镜头里的真实浇灌出了一朵黑暗的花。
60年代人,出生在浙江金华。卢广赚到了第一个十万之后,决定收手不做了。正如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钱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他不像很多人那样,赚了十万的想着百万,赚了百万的想着千万。93年,揣着十万块钱的卢广来到清华进修摄影。那个时候,怀里揣着两台美能达相机的他还觉得自己特牛。但是,跟人一聊,就傻了,当时,他的同学们都已经在用佳能、尼康了。当下,卢广用其中的四万五买了相机和镜头。
求学的两年,日子过的很清苦。买设备,交学费,还要吃饭。越来越少的钱。那个时候,他们进修班20多个人就住在清华校园内的地下室。五块钱一天。睡得的是上下铺。那个时候,正牌的清华学生都睡在楼上,整个地下室的通道睡得全是像卢广这样的进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