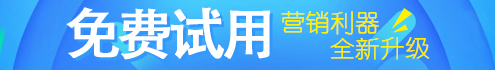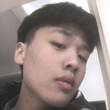默默记录这个时代
还没当兵那会儿,我经常跑去成都外文书店,但也只看得到如阿尔巴尼亚画报、朝鲜画报等社会主义的东西。直到我来到部队,因为(当空军)都在天上飞,就有机会飞到海南岛去买录音机,看到人们穿着大喇叭裤,戴着蛤蟆镜……那个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觉悟,很快一批手上有自己相机的人就“哗哗”起来。当时就觉得天变了,不再说只有新华社、画报社才有权利拍照片,每个百姓都可以。当然,也有不少年轻人以其他的方式,比如听老崔的那些音乐等。最重要的是人心打开了。
当兵那几年,除了将每月不足10元钱的津贴用来买胶卷,我还用来购买摄影资料,订了不少如《大众摄影》、《国际摄影》等杂志。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法国有个叫布勒松的摄影家,用莱卡相机拍摄他熟悉的巴黎;一个叫卡什的加拿大人,拍摄了“二战”时期自信坚定的丘吉尔。
除此之外,我自然也深深受到当时“四月影会”中,如罗晓韵、王文澜等摄影师作品的影响。有一次,我还差点把写好给罗晓韵的信寄出去,当时就是想要拜师什么的。
因为部队的关系,后来有机会认识了当时解放军画报社社长林庭松,以及那批在画报社里有名的摄影记者,车夫、李前光等等。当时他们桌上习惯放一把十字角尺,经常用来剪裁图片。我最初也还学着他们做了一把尺子,也裁。但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开窍,发现布勒松他们的照片全部有黑边框的,我也就远离了这样的一种做法。
包括***一版的《我们这一代》,收录的每一张照片都没动过。按下快门那一刹那就意味着裁剪完成。如1983年拍摄的《8521部队,我的战友们》这张照片,我当时用闪光灯补了,这样一个构图显现出他们当时的神态多有意思。这还需要再做裁剪吗?
同年冬天,我在包家巷成都妇产科医院门口,拍摄了那张漫天飘落的雪花的照片。我当时在相机底片袋上取了一个题目叫“降”。所幸,这次全新编辑,又找了出来。当时的情境我还记得特别深,那天我穿着工作服,骑自行车刚好到医院门口,看见漫天飘落的雪花,我想我们人类不也像这样,来到地球上吗?那时候的拍摄,其实仍然有一些曝光不足。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初学者,技术反而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眼里看到的,心里触动的那种感觉最重要。
当然,那时候也有一些没能拍到,现在回想不免后悔。
萌发出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自觉意识,其实就是从纠结是否拍摄西单民主墙时开始的。那个年代,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吸引或者干扰一个摄影师,打比赛、得奖、沙龙甚至摄影协会,这些都是立刻能够看到好处的,而且它们的势力一点不弱;但很多东西当时看不到好处,比如默默记录这个时代。

1983年,海军杭州疗养院。肖全拍摄了第一位文化人物、电影摄影师黄绍芬。
在部队除了有机会到处飞来飞去,拿着相机到上海、广州、海南岛的街上拍,那会也在杂志上看到不少室内人像摄影,对我的吸引力也挺强。
1983年在杭州疗养期间,我认识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老厂长徐桑楚和电影摄影师黄绍芬,我最早的人像拍摄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相片洗出来后,他们都非常喜欢。前辈的鼓励,也使得我后来对拍摄人像有了更大的兴趣和信心。
参与者,见证人
超期服役两年后,我从部队退下来。回成都,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谋得一份工作。那就像一个真正的工作室,主要做一些电视录像,拍摄老师课堂讲学情况等等。虽然工作挺无聊,但手上有一套公家的机器和一个暗房,对我来说,还是有很大吸引力,也有时间可以拍点自己的东西。
工作之余,我就开始模仿布勒松他们,拍摄自己身边熟悉的城市。当时没人给我这个任务,也没人告诉我这个城市很快会拆掉,应该拍。
从西方摄影师作品中,得到一种方法,一种当你的国家在发生改变、变革的时候,你要能清晰感受到它,而不是在那个时候去拍一些花花草草。当然花花草草也很漂亮,也不是说不能拍。肯定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
同时,我也开始与成都一些文化人如何多苓、翟永明、周强、钟鸣、万夏等,交上朋友。我喜欢他们,也经常给他们拍照。那时就感觉,诗人热爱自己的诗歌,画家热爱自己的作品,每个人都很幸福,而且也能感受到他们是真正敢于表达自己感情的第一拨人。
接近1990年,在钟鸣与赵野等人编辑的“地下刊物”《象罔》上,我见到了美国诗人庞德的照片,使我起心动念要为中国的文化人拍出既能感动我,又能感动别人的照片。其实在这之前,我拍摄肖像的意识已经有了,但仅是喜爱,并没有一个特别高的目标。也可以说,之前拍摄的那些肖像其实是积累的过程,直到看到庞德的照片,算是一个引爆,有一种顿悟、质变的感觉,接下来该做什么,一下就变得清晰起来。
那时候也觉得不能再守株待兔了,1986年拍北岛、顾城,也是因为星星诗歌节他们来了成都。1991年我辞掉铁饭碗。现在回想挺冲动,家人当时托不少人,各种关系才找到这么一个稳定的工作。
我清楚知道自己还是要走,当时一方面对自己已经有足够的信心,同时内心不少冲动都已经无法战胜,觉得再在成都待下去,自己接受不了。
《我们这一代》拍摄计划除了得到朋友的鼓励外,包括赵野、钟鸣、吕澎、柏桦等人也亲自帮我定拍摄名单。某种意义上看,它也是集体的智慧。这个系列最早的题目———《参与者与见证人》是万夏帮我取的。他当时对我说,你天天跟这帮人混,既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
当时,拿着已经拍摄的一些文学艺术领域的先锋人物,如诗人北岛、顾城以及作曲家何训田、画家何多苓,将他们的照片塞在一个文件夹里,每张照片下面写上艺术家的名字,贴了个题为《参与者与见证人》的封面,背在行囊里就出去了。
从个人经历来讲,高中毕业出去当兵的6年时间里,我接触的全是军人,完全不懂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开始的时候,就通过万夏他们帮忙引荐。后来,又如吕澎帮我介绍到长沙的美术圈,而他们又给我介绍了作家何立伟,而后者又帮忙写信介绍了苏童、叶兆言、陈村等等。就像一扇一扇窗子不断被打开。
贫困年代的同路人
1990年左右,当时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创始人吴少秋了解我的想法后,决定帮我出这本书。1993年,我们签署合同,总稿费两万五,他给我预支了一万。我就拿着这笔钱去了北京,经常和唐朝那帮人混,在他们家里打地铺。也会在东单那片,一家柏树旅馆,住那的地下室。街对面就是新王朝酒店,但我只有那点钱,不可能住到对面。
必须达到一定拍摄量才能出书,当时也是不断坚持,听朋友说谁厉害、出名,就去敲门,就去拍摄。比较遗憾,无奈错过的有。好些在国外的,如阿城等都没拍,其实这中间也有不少蛮重要。
在拍摄谁的问题上,我有自己所谓的历史观,包括张艺谋、姜文,他们的电影在中国那个时代,有很大的先锋意义,他们也都是有独立思考的人。另外,人选上也不是说只要是普通明星就去拍,这里面没有说相声的,其实他们中有不少人也特别有名。
我的选择还是那些对中国当代文化艺术有推动作用并独立思考的一拨人。
也不能说遇到困难,只不过在拍摄完诗人食指(郭路生)的时候,我被他的那种状态震撼到了。当我从芒克那获得郭路生的准确地址时,心里开始激动甚至感到不安。一个曾经写下《相信未来》,拯救不少知青的诗人,却被关在疯人院。
1993年8月27日下午2点,我去拍他,还用录音机录了他的诗。他看上去特别正常,却说自己是疯子。他的状态给我触动太大,我一度打电话给吴少秋不想再继续下去。
那个年代现在回看的确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说那个时候贫困,其实也是相对的,因为那时的年轻人,听到了崔健的音乐、唐朝的音乐,看到了很多有思想的小说,看了张艺谋的电影……
恰恰我觉得今天,要说贫困的话,精神上的贫困更甚。我的好朋友欧宁,当年在深圳,他知道我喜欢《辛德勒的名单》的电影原声带,就送了我一张,封壳上还给我写了两句话,“在战争年代,是上帝带领我们脱险;在贫困年代,是精神**我们上升。”
决定性的情绪
对于《我们这一代》,到现在其实我也并不觉得它有什么独特。当初它就是我的一个念头,就觉得中国的艺术家应该有像庞德这样的照片,于是花了十年去做这件事。
拍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首先是足够真诚。走到他们面前,他们很容易阅读到我是怎样一个人,是装不了的。所有的一举一动,说的每个字,包括呼吸,他们轻而易举可以感受到,他们是那么优秀的艺术家、作家。当他们看到了你,信任,就放心了。
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和我成为朋友,拍摄时很放松,自然而然流露出真实的东西。那些东西可能今天看起来依然特别感人。那种感觉有点像我早年看到庞德的那张照片,庆幸我没有白受他的启发和震动。
我是个特别感性的人,或者用李媚的话来说,我有一种很难形容的温存。不管拍什么都好,我觉得还是来自内心的感受。心比较善、比较细,所以我的影像里可以反映出很多很多的爱。张海儿曾和我说,如果他和我同时拍摄女孩,他的题目一定是坏女孩,但我拍的就类似伊斯兰那样,略带点小凄凉的一些照片。它们可能也是我内心的一种投射,自己内心也会有点忧郁、小孤独等等。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你内心影像的投射。比如,你为什么会选择那样的背景、你为什么会选择那样一个刹那的快门。布勒松说是“决定性的瞬间”,我觉得可以看作是“决定性的情绪”。长期琢磨了一些事情后,我觉得很多的照片都有特殊的情绪。三毛的图片、易知难的图片等等,这些是决定性的情绪,是内心的呈现。构图等很多东西可以学布勒松,但我的照片里,更多是可以透过照片,看到所谓灵魂深处的东西。
我对这些东西更加着迷。
拍摄《我们这一代》的十年,自己基本处于一个不断漂泊的状态。直到1995年去帮杨丽萍拍电影时,我离开了曾供职的深圳一家杂志社。那时已不想继续在媒体工作,还是想完成自己作为一个独立摄影师的路子。但那时又很难获得一个基金的赞助,或者可以去像马格南图片社那样的地方。
1996年,完成系列拍摄后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其实非常难。虽然《我们这一代》出版了,但它并不能给我带来足够的收益,我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哪混以及饭票从哪来。即便到了今天,如果有别的方法,我也可能会去尝试。但到目前为止,去年底新出的《我们这一代》,虽然展览和书籍都有很大影响,但我仍然要面对银子从哪来的问题。我现在也仍然会去帮朋友拍广告,我仍然不会拒绝他们。
1996年后,我做了很多让步,去拍商业拍广告,糊口。到现在,我并没有觉得摄影让我富裕。对于一个以摄影为业的我,现在依然面临着这些问题。毕竟不像那帮当代艺术家,他们一幅画卖几百万上千万,摄影做不到。
直到走不动
近些年,我到了世界许多地方,绝大多数都不是自己自费可以去的,往往都是参与各种活动、展览。已经很难再像拍摄《我们那一代》那样,带着强烈的目的性(去拍),多数情况都只是带着一贯的想法。
或许是肖像拍得比较多,不少人把我归到肖像这个领域来,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赞美。但我感觉(自己)不仅仅受限于肖像的概念,包括这几年到世界各地拍的作品,也不只是肖像的概念。
前年,我和吕澎、王广义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聊天。一个老太太和一位金发女人搭肩走过,一看就是一对母女。我当时只带着一个35mm的定焦镜头,拍了她们的背影。非常动人,有意思。我就觉得应该拍一个“Together”(在一起)系列,后来就在威尼斯、佛罗伦萨以及巴塞罗那,完成了一组“在一起”那种感觉的照片。
我并不在乎我的拍摄方式是不是就是纪实摄影,它是什么,我对这个事情本身不感兴趣。我只知道我用的是一种报道摄影的方式,并且今天仍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拍照片,亦足够让很多人看到照片感动。
老爷子马克·吕布一直在世界各地工作,每年、每年,直到他走不动。2010年,那一年他已87岁,还来到上海开展览。3月份,上海特别冷,还下着雨,在黄浦江边的一个楼上,我感觉他持着相机的手都在抖。他真的需要多那一张照片吗?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他一直在用自己的相机见证一个时代。虽然他曾说过,摄影其实没那么神秘和重要,就像一个人在公共汽车上说过的一句话。我觉得这是他的谦虚。布勒松、马克·吕布,他们的一生,他们的画册,至少是对这个时代极其重要的记录。
我觉得我仍然在走自己的一条路。无论是我曾经拍《我们这一代》,还是之后我为了作为一个正常人、一个摄影师的生命的延续,拍了大量之前我曾嗤之以鼻的商业照片。但我现在觉得,我根本没有理由去嗤之以鼻,我认为商业摄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领域。除了拍摄当年一拨文化艺术圈的那代人,我***没有落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留下了很多灿烂的影像。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勤奋的摄影师,至于谈论我的其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像布勒松、马克·吕布一样,为了自己的国家,留下很多的影像。
在马克·吕布八十岁生日时,我送给他一份礼物,送给一个80岁还在拍照的老人。我说,我亲身感受到了,您作为一个摄影师是如何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
都说马克·吕布只能让人敬仰却难以效仿,但我偏偏想要去效仿他。这是我非常强大的一个动力,我肯定不会像很多人那样,到了六十多岁就觉得自己废了。我肯定会像马克·吕布一样,直到走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