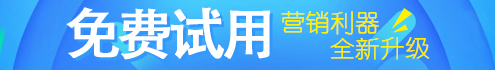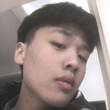之所以用野生定义张宁,因为他非科班出身,在这之前完全没想过做摄影;开始拍照了,也没去混所谓的摄影圈;此外他的视角和状态,也都是野生的。
2017年年底,张宁、老王两口子把做了八年的咖啡馆转手,四处晃荡。完全没想过做摄影,一次店里活动,朋友来拍照,张宁忽然觉得有点意思,就弄了个微单,试试看。“好像是有个定理,你在某个专业领域是个白痴,什么都不懂,你的进步非常非常快,那个叫愚昧高峰,那个时候我进入一个顶端,觉得自己拍照好牛逼,那个时候,每天拍照修图,然后发上去,等着人家来点赞,虚荣心爆棚,没有100个赞,晚上都睡不着觉(笑)。”
他自己说是愚昧高峰,说自己是白痴,其实,不是这么个事儿。他在杂志工作过,有知识储备,有一些通识,有视野,有能力在日常的世俗世界里发觉捕捉到美感,在面对的任何世界里都能找到这种美感,恰好,这个时候他拿起了相机,有了表达工具和出口。
老王说之后他们拍的很多地方,大家留言*多的是:“怎么感觉我们去的不是一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观看视角不同,不管去哪里,张宁都有自己的视角,他的拍摄角度,别人永远偷不到。“别人的拍摄角度,我也偷不到。我会看人家好的作品,但我拒绝学习别人的构图,网上很多课程,教你如何构图,构图怎么学啊,你不可能学得到啊。”
张宁说他希望拍出陌生感,当地人的陌生感,“比如你一直在成都,你很习惯成都的街道,我拍了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原来还能这样,这就是陌生感。”当时他在强巴林寺拍了很多辩经的照片,后来全删了,他说一旦放大,就觉得没意思,他说现在只要看到西藏经幡的,都觉得很没意思。“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希望去地域化,拍出新意出来,不要一直是那个东西。有一种暗藏的小心思、小趣味,但不要直接暴露到你面前,它有寓意在。”拍大事件、大场景,有另外的人去做,张宁说他不希望把精力消耗在这里,他要的是舒服、有温度的东西,要自己的视角。
前些日子张宁去香港工作拍片,回来后问他交到朋友没,他答:“我不喜欢交朋友。”采访的那天,他讲起这个场景,接着说:”其实在那种状态下,是应该要去交朋友的,你交了朋友,可能你的活会更多,你的人脉会更广,但我觉得,我不交朋友,我自己会更舒服。我舒服,更重要。”很多时候,这是他在人群中的状态。把该拍的东西拍完,没自己的事情了,就出去兜风了。“大家互相加个微信,交换名片,没事混混圈子,加各种群,很累,不干这个事情,我也能活得下去,那我宁可选择不干。我也不觉得好像不混摄影圈,我就活不下去,我就拍得不够好,一定要混摄影圈,我才能进步。”
这么个德行,就有了野生的状态,有了自在舒展的,不卑不亢的照片。